盛可以擅长通过身体故事完成对社会心理、权力结构以及灵魂深处的剖析。她新近发表的小说《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》,我反复读了三遍。读第一遍,扎心;读第二遍,潸然泪下;读第三遍,想找人说话却身边无人。但我相信,此刻即使红袖添香亦将默然无语。
小说中,少女时代有强烈弑父情结的“我”,唯一梦想就是“父亲死掉”。在“我们”看来,父亲是阴霾重重的传统,是飞扬跋扈的权力,还是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。母亲遭受的家暴、哥哥姐姐的贫穷、“我”的弃学等等。
我的父亲和小说中“我”的父亲,有着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。父亲于青少年时期的我,也是“一个遥远的符号,一个概念,一个称谓,一个背景”。同样感受到父亲大山般的统治力、阻挡力,不同的是,我对父亲的反抗并非拒绝、出走、冷落,更不是语言“围剿”,而是正面“迎击”——发奋读书。有一次,我考试得95分,父亲拿那丢掉的5分说事。我排名第五,父亲责问,为什么进不了“前三”?到初高中阶段,我囊括所有考试总分的前三名,终于有机会看到父亲心花怒而不放,宁可沉默也吝啬褒奖的尴尬。
小说中的“我”,对父亲的仇恨,细究起来是一种逻辑自洽。“我”的反抗既“审父”又“弑父”。父亲壮年时,避而远之,不闻不问。年老多病时,不依不饶,“紧攥着父亲对我们的亏欠不松手,有意要父亲反省”。所有人都放大“父亲”的冷硬,无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;所有人都控诉“父亲”的颟顸,从不关心他身体的衰败。
“父亲”被抽象成专制的代名词,因此,无处不在的冷漠,堂而皇之地成为抵御“暴政”的铠甲。想到互联网海量声讨“油腻中年”及“为老不尊”的爆款文,我为“我”父亲,也为作为父亲的我感到深切悲哀。不知道我的子女是否也像“我”那样,隐匿着弑父的冲动?
人类真的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,天生具有“弑父情结”吗?检索中外文学史,“弑父”,在西方文学是贯穿各阶段的主题,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伊凡、《变形记》里的格里高尔;反观中国文学,“尊父”则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前二千多年的基本伦理。被称为最有叛逆精神的《牡丹亭》《红楼梦》中的杜丽娘、贾宝玉们,只不过是在人生选择方面有违“父愿”,并无摆脱被统治、被支配,进而掌握家庭和社会主导权的自由意志。
“五四”以后的女性作家,呈现从“弑父”“审父”,到“寻父”“恋父”的发展脉络,与同时代的政治进程、文化心理、妇女解放大致吻合。作为“70后”女性代表作家的盛可以,不同于魏微对父辈的着迷,不同于梁鸿对父亲的体恤慈悲,不同于鲁敏之父亲的永远在场。《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》承续白薇、丁玲、张爱玲的精神血脉,一上来就“弑父”,但并不彻底,有点像萧红,弑父,更恋父。盛可以的弑父之剑,生硬凛冽,抽刀断水,却劈不开死亡之河。
活着的“父亲”,只是一个符号。“父亲”的死,也不过是那个符号的加强。“弑父”未果的“我”,在父亲死亡这件事上,仅有一丝“心绪不宁”,转而顺利完成一场隆重而如意的葬礼。
时隔不久,死亡之河逆转了“我”的灵魂方向,死亡之镐也挖出了“父亲”的脆弱。“我”发现,当一个人彻底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时,竟如此和颜悦色,像冬夜里缓慢燃烧的老树蔸,像母亲侍弄的菜园子那样整齐朴素。
“父亲”的死,是一架灵魂显微镜,显现了“我”的自私、冷漠、刻薄,放大了我们为父亲有意挖掘的代沟。惯于独立自主的“我”,终因“父亲”的死,生发“寻父”“恋父”的渴念。标榜诗与远方的我们,也必因父亲的撒手而四顾茫然。
“我”与父亲的对抗,止于父亲的死。我们的自我纠察、自我厮杀刚刚开始,也许更痛楚、更惨烈。
的确,活着的父亲,与我们往往无话可说。我们总以为,适合说话的人在远方。父亲死了,我们才明白,“最大的痛苦无法言说,最深的愧疚难于描述”,最有效的缅怀是沉默,最彻底的自省是沉默。此外,十指穿心的痛也只能以沉默来治愈。
值得一提的是,小说以“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”开始,以“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吗”结束。灵魂的大转向,难道非要经过死亡之河的冲击?我认为,作者处理这个疑难,未免仓促。好在充满隐喻的结尾,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。“父亲”遗物中的书籍以及用绳子捆绑的病历本,无疑是“父亲”的精神遗产,它统治一切、扛起一切,也承受一切、救赎一切。
“父亲”在病历中复活,在“我”记忆中那啄木鸟般无力的砍斫声中爆发能量,在“我”深深的想念里显现荣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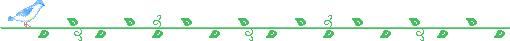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曹文军
编辑:刘璐



请输入验证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