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初中时,有两篇课文印象特别深刻。一是鲁迅的《秋夜》,开篇是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另一篇是郭沫若的《石榴》。我家的前院也有两棵树,一棵是柚子树,另一棵是石榴树。老师在讲解课文的时候,我感同身受。
那时,老家的院子很简陋,没有围墙。房子坐东朝西,门前有一块晒谷坪。晒谷坪南面是厨房,北面是邻居的厨房。晒谷坪另一侧是一座简易的杉皮木棚。木棚一端是父亲的木工作坊,另一端是鸡鸭圈舍。那两棵树穿过木棚,茂盛在木棚之上。树的躯干像是木棚的立柱,但并不妨碍树的生长,反而很茂盛,年年果实满枝。
柚子树高而直,像一把伞。果实很多,但并不甜,即便完全成熟,也是酸涩的。但家人们依旧喜爱,奶奶会把柚子皮制作成一道非常好吃的菜。柚子成熟后,就用竹篙把柚子敲打下来。奶奶将柚子皮取下,削去最外层绿色的皮,切成条状,然后淖水,再放在清水里揉搓,去苦涩味。晾干水分后,加适当的香料粉、辣椒粉和盐搓一搓,再加豆豉充分混合,密封在坛子里腌制。腌制好后,从坛子里取出一小碗,搁上一些猪油渣,再淋上一点香油,待鼎罐煮饭滤掉米汤后,放在饭面蒸。饭熟则菜好。盛饭时,揭开重重的鼎罐盖,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,令人垂涎三尺。那时,只要舀上一小调羹,拌在饭里,就能美滋滋地吃完一碗饭。这道菜因为贮存在坛子里,可以有计划地吃上一年。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持续打霜和结冰,柚子树被冻坏,有近一半的枝叶干枯。第二年只是零星地结了几个柚子,且果实瘦小。第三年,柚子树完全枯死了。枯死的柚子树容易生虫,父亲很不舍地将它砍了。枝叶做柴火,主干锯木板打成了简易家具。
院里的另一棵是石榴树。石榴树生长在木棚的最西面,紧邻古道。一半的枝叶在古道的上空。由于石榴树果实特别多,等果子长大后,枝条便耷拉下来,上面挂满了红绿相间的石榴果。石榴果完全成熟后,会自然裂开,像一张张笑脸,露出一口晶莹剔透、满是汁液的石榴籽,煞是诱人。很多路人经过石榴树下,难免经不住诱惑,顺手摘下一颗。时间久了,几乎有一半的果子回馈给了路人。
有一天中午,奶奶正在厨房做饭,听到外面有异响。走出来一看,发现一名年长的路人正用长长的木棍敲击高处的石榴。奶奶咳嗽一声,路人警觉,丢下棍子,站在那儿,一脸羞愧。奶奶走上前细声问道:您要吃石榴吗?路人慌忙摇手说道:“是这样,我家孙子最近一直闹肚子,中医给了一个方子,需要石榴皮,刚才见到您这儿的石榴,一时性急,就想敲一个下来带回去。”奶奶得知后,二话不说,顺手在院子里摘了几个大大的石榴塞在路人手里。路人很是感激,连声说:“谢谢。”
石榴味甜,略带一点酸味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棵挂满果实的石榴,无疑是家里老少的挚爱。
石榴的花期很长,果实成熟的周期也长。有的果子成熟了,有的还只是花蕾。每天起来,我们这些娃儿就会在院子里仰起脖子,细细查看那些果子。看到有裂开的石榴,就惊喜地嚷道:“开了,开了!”大人就会将开裂的石榴摘下来、掰开,分给我们。娃儿们就坐在门墩上,细数那一粒粒酸甜的籽儿,放在嘴里,用牙轻轻地挤破它,任汁液在口腔里跑。有时会一粒粒地积攒起来,然后一把塞进嘴里,再猛地一嚼,那满口的酸甜会令人忘乎所以。而大人会将我们吃剩的果皮收集起来,放在窗台晾晒,以便送给那些需要石榴皮做药方子的邻里乡亲。
也许是树龄已高,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,石榴树被拦腰折断。大人见状,很是惋惜。想不到这棵陪伴家人几十年、给家人带来无数甜美记忆的石榴树就这样倒下了。父亲没有将石榴树桩清除,找来几十块青砖,砌成一个花池,将石榴树桩围好。岂知第二年,树桩周围竟然长出了嫩芽。多年之后,一棵更为蓬勃茁壮的石榴树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时至今日,石榴树生命力一直旺盛,每年都会结出满枝的硕果。
院子里的两棵树给了我太多甜蜜的回忆。如今,无论怎样的山珍海味、佳肴美馔,都抵不过被浓烈的亲情和乡情烘托出来的滋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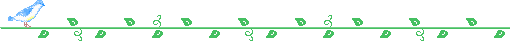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何发祥
编辑:张惠娟



请输入验证码